2024年坎城影展,由評審團主席《Barbie芭比》導演葛莉塔潔薇(Greta Gerwig)頒發了最佳影片金棕櫚給美國獨立製片導演西恩貝克(Sean Baker)執導的電影《Anora》,這份得獎名單可說是自去年《墜惡真相》大快人心的女性電影勝利後,坎城影展再次在評論圈有口皆碑的勝利。筆者試圖整理數部得獎電影的短評,並將針對「什麼是競賽?」的思考與讀者分享。
2024年是一個多變年份,「AI起飛」又一次帶給台灣和世界震撼,世界彷彿反覆告訴我們需要與過往的模式告別。即便如此,今年大多數千禧年前後崛起的男性導演,與一些老牌大師,則用盡了生命不斷的在電影中「強調」一些「事」與「物」,卻不見得奏效,只顯得蒼老、無力、無能。相較之下,節奏躁動、歡快、無與倫比的最佳影片《Anora》導演西恩貝克在得獎記者會不斷強調「獨立電影」必須要存在於「主流院線」,其實《Anora》卻在潔薇率領的評審團中引起討論,評審記者會上他們提到這部片令人想起劉別謙、霍華霍克斯等許多影史經典文藝片。

▲中國名導賈樟柯《風流一代》於今年坎城首映。(圖/坎城官方)
因此,實體電影院與串流的戰爭,相對於「AI時代」帶來的「罷工」與「產業革新」的新穎,這個討論似乎顯得過時;但仔細想想與法蘭西斯柯波拉《Megalopolis》的操作相比,讓舞台演員上台跟電影演員對話的「現場表演」,這聲嘶力竭、不忍卒睹的電影與戲劇「跨界」,似乎就顯得我們還沒有真的處理完,我們時代的問題。

▲大師法蘭西斯柯波拉帶著新作《Megalopolis》在坎城影展放映。(圖/坎城官方)
仔細想想,「物件」的使用,「後設」討論電影本質、甚至觸及當代人「社群媒體」焦慮,是今年坎城電影的公約數。「後設」電影如,令人愉悅的法國電影《Marcello Mio》找來義大利巨星馬斯楚安尼的女兒帶著「假髮」扮演父、cult片傳奇大衛柯能堡《The Shrouds》中用來悼念亡妻的XR高科技「裹屍布」、保羅許瑞德《Oh, Canada》美國加拿大「邊界線」,則讓他用反覆的蒙太奇暴力,釋放對自己生涯的悔與恨。七零年代大師導演需要多少明顯「物」,才能成功穿透讓我們感覺到他們的焦慮呢?Ali Abbasi《The Apprentice》沒有沈溺在川普手上的類安非他命減肥藥,影評普遍嚴苛,批評他這次選擇用這種方式「黑暗風格」,沒選邊站,毫無效果。實際上這部片的美學手法、調度上的成就與《Holy Spider》相去不遠,選材和政治性的操作還是最頂尖影展舞台的一個不能說的秘密。
更別提,女性主義剝削電影《The Substance》片尾大撒的血漿、奧斯卡得主索倫提諾讓城市具現化沉魚落雁的美女《Parthenope》在結尾消失為一只「泳衣」,筆者以為這些毫無效果。;寫實主義電影《Wild Diamond》偷香水換錢買「水鑽」讓ig限動閃亮亮,《風流一代》故事結尾出現的AI機器人,可能是本片稍微接近這個充滿「社群媒體」焦慮的2024年的片刻,同樣意義薄弱。歐迪亞的西語歌舞片《Emilia Pérez》、和《The Substance》的「場面」令現場觀眾影評一片叫好的大快人心,可能來自這兩部片的輕盈,對照普遍電影沈溺在如何告別過去的聲嘶力竭。
「什麼是競賽?」不少大師作者用盡生命叩問存在的意義,於此同時不少導演用盡生命擠進坎城競賽,這些聲嘶力竭卻不一定真正告訴我們電影的「競技」意義是什麼。筆者仍舊肯定?今年普遍令人沮喪的電影中,少數珠玉提醒我們,坎城作為電影藝術最高殿堂,如同其他「競技」運動,藝術的競技意義在將舞台化作交流的平台。在看似全面迎向主打去中心、去階層化的新時代,我們其實還沒有完全準備好回答「一個沒有競賽的時代」對導演是什麼、對觀眾又是什麼,因此我們還是得暫時堅守過往影展競賽的原則和信念。今年許多競賽電影的爽快,只圖一個政治性、視覺感,就像是一個過長的高級的廣告,或一部沒有太大尺度的「porn」。碰巧今年是時尚品牌「聖羅蘭」首次投入電影製作的年份,四部競賽電影由他們投資出品;而政治電影在法國與坎城影展,更時常是有政治宣傳目的,能滿足慾望的效果,伊朗導演Mohammad Rasoulof《一念菩提》可說是未演先「高潮」。
以下是得獎電影短評:
特別獎:《一念菩提》(The Seed of the Sacred Fig)by Mohammad Rasoulof (評分:3.5/5)
Rasoulof從來就不滿足於只拍一部電影。而伊朗政府卻一部片都不讓他拍。
故事描述在在伊朗革命法院剛升上檢察官的父親,升上法官的生涯也不遠了,然而檢察官生涯剛到任,就遇上「頭巾革命」,每天都要提告「處死」很多人,在家中兩個青少年女兒卻不了解狀況,女孩們保守的母親在中間「女人為難女人」。故事開演一陣子後,家中各種張力陡升,家中配槍無端失蹤,故事開始像極了一部法哈蒂式的「風暴」電影。
電影千回百轉,場景一換我們又進入不同類型,世界首映現場,電影後段三度全場為劇情大快人心鼓掌,電影結束更有十四分鐘不間斷的掌聲(Standing ovation)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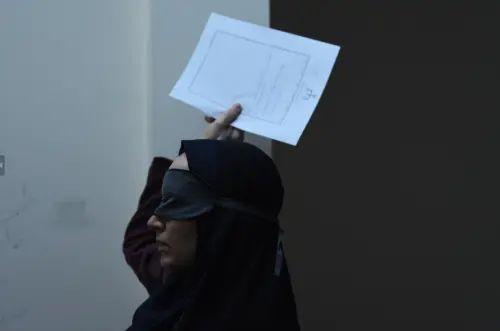
▲《一念菩提》(The Seed of the Sacred Fig)。(圖/坎城官方)
伊朗政治局勢的演變與藝術審查的惡化,來得又急又快。阿巴斯走了、醜聞被爆出;伊朗政府繼續緊盯潘納希疫,他還繼續拍;法哈蒂幾度登峰造極。
2020年,疫情前的最後一屆柏林影展,《無邪》最後一部競賽片放映,一舉奪得金熊獎。四段式電影,圍繞著監獄發生的四段故事,死刑行刑官、逃兵、執行死刑的士兵...,直接了當的對獨裁政治的審查做出了很好的批判。怎能不動容?當年有很多人很討厭這部片。政治批判電影和政治宣傳電影(propaganda)只有一線之隔。Rasoulof從來就不滿足於只拍一部電影。當伊朗政府卻一部片都不讓他拍。
伊朗在疫情後發生了因為「頭巾革命」有了因女權而起的大規模各種社會示威,擴及範圍之廣、程度之深、延續之久,這不只是女性主義運動,卻是能根本性地針對地方貪腐、特權階級、世代革命,法哈蒂時代的伊朗電影單向的倫理劇可以蘊含的複雜問題,如今全面向的爆發,我們也不用再通過單一窗口認識伊朗了。
Rasoulof 這次拍了快三個小時的故事,幾乎只發生在車上、一間市區住宅、鄉下小屋,毫無早期作品的生澀、習作、臨摹感,也沒有《無邪》、《不能說的再見》的因陋就簡,對我來說更多的是《正直好人》裡面那種典型的男性創作者在情節電影上面對「體制」的憤怒時,能否適度平衡電影感與正義感的拿捏。這次一點都不枯燥,甚至很像商業電影,很法哈蒂,有些典型坎城爆紅政治電影的氣味。但,這部片的賣座與口碑,太過商業、太過反正宣(變成另一種政宣),這些疑惑最終都會會與作者真正的赤誠錯身而過的,因為Rasoulof從來就不滿足於只拍一部電影。因為,Rasoulof從來就不滿足於只拍一部電影,他下一部電影將在德國漢堡開機。就像電影的片頭字卡提示我們的:菩提的種子會在寄主樹上發芽、抽枝、茁壯,逐漸將其窒息;然後,新的菩提樹就獨立存在了。或許,美學上,這就也是無論在哪塊土地都能發芽土壤的一種方式。
評審團獎、女主角獎:Adriana Paz, Karla Sofía Gascón, Selena Gomez, and Zoe Saldaña《Emilia Pérez》
《大獄言家》賈克歐迪亞(Jacques Audiard)有口皆碑的《Emilia Pérez》,實際上是四個女演員一起拿獎,但「跨性別」演員Karla Sofía Gascón上台領獎時卻誤以為是自己獨得影后,只因歌壇天后Selena Gomez和資深演員Zoe Saldaña都未到場領獎。
《Emilia Pérez》描繪來烘托一個黑幫大佬想要變性、贖罪的故事。片名已經暗示故事主角是誰,但本片確實沒有一個明確的主角,讓這部借用了墨西哥幫派暴力背景的西語歌舞通俗劇,儘管加上了主要人物Emilia變性前後的心路歷程,為讓在Emilia身旁的女人,被綁架的女律師(Zoe Saldaña)、Emilia Pérez還子的母親(Selena Gomez)、現在身旁的同性戀伴侶(Adriana Paz),來烘托變性與贖罪的故事。實際上,如果沒有歌舞場面,沒有大牌明星助陣,相比熟稔這類類型操作的阿莫多瓦,儘管Karla Sofía Gascón投注了自身迷人的「跨性別」經歷,歐迪亞這次在寫實主義故事的疏忽與傲慢,其實是顯而易見的。即便如此,筆者還是替如此「男性」的導演,在主流電影舞台,為性別多樣敘事盡一份心力感感到開心。

▲評審團獎頒發給了《Emilia Pérez》。(圖/坎城官方)
男主角獎:Jesse Plemons《Kinds of Kindness》
尤格蘭西默《Kinds of Kindness》其中一段故事讓整片「肝臟」癱在地上,才能說明這部片,就是他的「婚姻故事」。但這也沒什麼,柏格曼的《婚姻場景》也是六個小時。別忘了《婚姻場景》電視迷你劇是。用當代劇情片的規模與規格,《Kinds of Kindness》獲得迪士尼旗下探照燈影業的支持,把一個適合影集多段的故事拍出來,確實是一番成就,更別提本片精彩的卡司Emma Stone、Willem Dafoe、Margaret Qualley、Joe Alwyn,影帝Jesse Plemons才在《帝國內戰:美國內戰》剛交出令人印象深刻的配角演出,就用本片大篇幅(實際上甚至跟Emma Stone一樣多)且精湛的戲份,獲得一座實至名歸的坎城影帝。
故事中晦澀的晦澀、深慟,讓人不禁擔憂起導演Lanthimos的演員妻子Ariane Labed,陪伴演Lanthimos走過數部希臘「怪浪潮」電影,在Lanthimos於英語電影的主流世界高飛時,更多年耕於導演創作領域。Labed首部長片《September Says》同樣入圍坎城,卻在「一種注目」競賽。《Kinds of Kindness》三段曖昧不明的故事,那麼廣泛無邊,高深莫測,令人不禁聯想起導演的生命故事;本片編劇是Efthimis Filippou,Lanthimos許久沒有再攜手的編劇搭黨,或許合作關係,也是一種夫妻關係的投射。
現場影評似乎都執著在蘭希默回歸早期風格的失敗,也沒人想認真討論明明擺在桌上,他要深入的「主題」,就像那片肝臟。
最佳劇本:《The Substance》by Coralie Fargeat
結合女性主義敘事與女性剝削電影獲好評的《The Substance》,電影片尾大撒的血漿另所以影評人人稱道,卻比較少人認真討論本片真正的「Substance」應該是女演員的身體,本片用樸實的敘事、平滑的影像,像是真的在一個「換身」物質的廣告片般的精緻,用寬銀幕的震撼,拍出Demi Moore對衰老的恐懼,和Margaret Qualley肉體的青春。老實說,這些我們都在柯能堡電影裡面看過。卻不曾用女性主義敘事來拍過沒錯。事實上,儘管獲得最劇本,但若想看Demi Moore和Margaret Qualley的雙女主演出,對身體政治做出視覺的詮釋,恐怕觀眾會失望吧。還不如去看Qualley前年的cult爽片《聖地》(Sanctuary)。由男導演執導,《聖地》在台灣並沒有上映Qualley在片中扮來自底層的SM女王,與小開上演階級翻轉的戰爭,這點與Qualley真實生活中的「星二代」身份互文,則更顯趣味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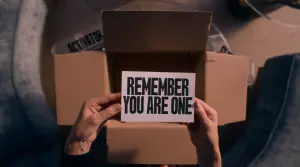
▲結合女性主義敘事與女性剝削電影獲好評的類型電影《The Substance》。(圖/坎城官方)
Miguel Gomes無疑的是許多影迷的英雄,這部片用一個逃婚官員、追逐他的未婚妻的故事,故事分為兩個部分,迷人的第一部分是大英帝國官員的部分,混雜了記錄、檔案資料、片場重演,美輪美奐。第二部分,則切換成追逐他的未婚妻的視角,重演更多了經典老片的氣味,故事層次更多,紀錄性的「旅遊文學」成分減少,詮釋人物心境功能則越來越少,越來越曖昧。
電影全片放映完,觀眾可能還需要時間咀嚼電影看似簡單,卻難以一言道盡的結局。這是一部讓世界大戰前、疫情前、疫情後的各種時間,用電影疊加、壓縮、釋放的現象學過程,殖民主義與後殖民主義是電影第一部分的切入觀點,但加入了不同性別、不同時間的向度之後,第二部分女性觀點的對照,究竟是解釋了、解脫了、解答了什麼嗎?Gomes無疑的拒絕給出明確的立場和直白的答案。讓這部,他首次攻頂坎城競賽的作品,成為他創作生涯中無疑「最困難」的一部長片。

▲導演米格爾戈麥斯(Miguel Gomes)靠《Grand Tour》在今年拿下最佳導演獎。(圖/坎城官方)
Payal Kapadia的《All We Imagine as Light》是一個看似比想像中更質樸的作品。《All We Imagine as Light》故事描述,一對護士室友,帶著各自的感情煩惱,幫著「被都更」的醫院廚娘搬家,各懷心事的三人來到海灘的舒心與解放之旅。許多人問,「這究竟有什麼好拍的?」實際上,我問這部片和阿比查邦《極樂森林》有什麼差別?導演自言,在描繪女性的慾望、印度社會對女性慾望的壓抑之外,這還是一個關於「友情」的故事,既然是關於友誼,就是「女人不要為難女人」的故事。
若看過導演一鳴驚人的「實驗」紀錄片《A Night of Knowing Nothing》就知道他不會輕易放棄社會批判。《A Night of Knowing Nothing》用實驗電影手法,後設自傳性質描繪的一起校園和平抗議事件,針對當時電影學院校長的抗議,後來被警察鎮壓,用詩意手法描繪「運動後」的PTSD和感傷。這層感傷,或許在《All We Imagine as Light》無法明顯看到,只剩下一小段「都更聯盟」集會,但導演仍舊是那個關注在大的社會變動下,個體之間如何連結、維繫、保護情感,照料且不擠壓彼此慾望空間的作者。

▲評審團大獎頒給印度女導演的《你是我眼中的那道光》(All We Imagine as Light)。(圖/坎城官方)
當坎城的我們(通常是男人)一邊在罵尤格蘭西莫《Kind of Kindness》太過男性、太過重複,回想年初,我們是怎麼面對社群上《可憐的東西》是否是「女性主義」的爭議,在這些對「性」、「潛意識」的討論越來越開放,我們還剩下什麼不能揭露的戰場?如果一個跟隨潮流的觀眾、一個探看風向的KOL既不能喜歡《Kind of Kindness》、也不能喜歡《All We Imagine as Light》,那他今年該推崇哪部片?《Anora》?對我而言,蘭西莫一路走來始終如一,儘管靠向好萊塢商業迷失了一些風格,但他和他的編劇夥伴對佛洛伊德的理解始終沒有長進,卻與其他坎城男孩俱樂部導演一樣,越來越是當今美學的領航者,今天能對他有這些反省,當然難能可貴。
我們對蘭西莫的反省,是建立在對世界各種族群、種族、階級脈絡下的女性主義創作者夠深刻的理解嗎?
辨識、慎選你的戰鬥,或許這就是友誼可以給我們的最好意義,《All We Imagine as Light》最美妙之處在於,即便她的女性主義討論基本,但踏實。導演甚至提到,他是為了「All We Imagine as Light」這句話很美,而把它加入電影台詞,在電影末段一場阿比查邦感強烈的場面中,而這也是全片我們看到從寫實主義過度到魔幻寫實的驚鴻一瞥。
這給我們一個啟示:或許,「魔幻寫實」的發生並不一定在創作上是來自極端嚴格的田野調查、完全正確的身份政治審查、絕對道德至上的社會關懷;卻可以是一個內在平靜寬厚的作者,來自私人的、文學的、感性的片刻,讓自己被想像成光,在電影現場,照亮影像。若電影的想像力能讓我們找到一個,化解當代性、後現代性、寫實倫理與形式主義衝突的可能曙光,我們汲汲營營尋找那道光,其實可能就是每天在那裡的日出、夕陽。
●作者:沈怡昕/影評人
●本文為作者評論意見,不代表《NOWnews今日新聞》立場
●《今日廣場》歡迎來稿或參與討論,請附真實姓名及聯絡電話,文章歡迎寄至:opinion@nownews.com
我是廣告 請繼續往下閱讀

因此,實體電影院與串流的戰爭,相對於「AI時代」帶來的「罷工」與「產業革新」的新穎,這個討論似乎顯得過時;但仔細想想與法蘭西斯柯波拉《Megalopolis》的操作相比,讓舞台演員上台跟電影演員對話的「現場表演」,這聲嘶力竭、不忍卒睹的電影與戲劇「跨界」,似乎就顯得我們還沒有真的處理完,我們時代的問題。

仔細想想,「物件」的使用,「後設」討論電影本質、甚至觸及當代人「社群媒體」焦慮,是今年坎城電影的公約數。「後設」電影如,令人愉悅的法國電影《Marcello Mio》找來義大利巨星馬斯楚安尼的女兒帶著「假髮」扮演父、cult片傳奇大衛柯能堡《The Shrouds》中用來悼念亡妻的XR高科技「裹屍布」、保羅許瑞德《Oh, Canada》美國加拿大「邊界線」,則讓他用反覆的蒙太奇暴力,釋放對自己生涯的悔與恨。七零年代大師導演需要多少明顯「物」,才能成功穿透讓我們感覺到他們的焦慮呢?Ali Abbasi《The Apprentice》沒有沈溺在川普手上的類安非他命減肥藥,影評普遍嚴苛,批評他這次選擇用這種方式「黑暗風格」,沒選邊站,毫無效果。實際上這部片的美學手法、調度上的成就與《Holy Spider》相去不遠,選材和政治性的操作還是最頂尖影展舞台的一個不能說的秘密。
更別提,女性主義剝削電影《The Substance》片尾大撒的血漿、奧斯卡得主索倫提諾讓城市具現化沉魚落雁的美女《Parthenope》在結尾消失為一只「泳衣」,筆者以為這些毫無效果。;寫實主義電影《Wild Diamond》偷香水換錢買「水鑽」讓ig限動閃亮亮,《風流一代》故事結尾出現的AI機器人,可能是本片稍微接近這個充滿「社群媒體」焦慮的2024年的片刻,同樣意義薄弱。歐迪亞的西語歌舞片《Emilia Pérez》、和《The Substance》的「場面」令現場觀眾影評一片叫好的大快人心,可能來自這兩部片的輕盈,對照普遍電影沈溺在如何告別過去的聲嘶力竭。
「什麼是競賽?」不少大師作者用盡生命叩問存在的意義,於此同時不少導演用盡生命擠進坎城競賽,這些聲嘶力竭卻不一定真正告訴我們電影的「競技」意義是什麼。筆者仍舊肯定?今年普遍令人沮喪的電影中,少數珠玉提醒我們,坎城作為電影藝術最高殿堂,如同其他「競技」運動,藝術的競技意義在將舞台化作交流的平台。在看似全面迎向主打去中心、去階層化的新時代,我們其實還沒有完全準備好回答「一個沒有競賽的時代」對導演是什麼、對觀眾又是什麼,因此我們還是得暫時堅守過往影展競賽的原則和信念。今年許多競賽電影的爽快,只圖一個政治性、視覺感,就像是一個過長的高級的廣告,或一部沒有太大尺度的「porn」。碰巧今年是時尚品牌「聖羅蘭」首次投入電影製作的年份,四部競賽電影由他們投資出品;而政治電影在法國與坎城影展,更時常是有政治宣傳目的,能滿足慾望的效果,伊朗導演Mohammad Rasoulof《一念菩提》可說是未演先「高潮」。
以下是得獎電影短評:
特別獎:《一念菩提》(The Seed of the Sacred Fig)by Mohammad Rasoulof (評分:3.5/5)
Rasoulof從來就不滿足於只拍一部電影。而伊朗政府卻一部片都不讓他拍。
故事描述在在伊朗革命法院剛升上檢察官的父親,升上法官的生涯也不遠了,然而檢察官生涯剛到任,就遇上「頭巾革命」,每天都要提告「處死」很多人,在家中兩個青少年女兒卻不了解狀況,女孩們保守的母親在中間「女人為難女人」。故事開演一陣子後,家中各種張力陡升,家中配槍無端失蹤,故事開始像極了一部法哈蒂式的「風暴」電影。
電影千回百轉,場景一換我們又進入不同類型,世界首映現場,電影後段三度全場為劇情大快人心鼓掌,電影結束更有十四分鐘不間斷的掌聲(Standing ovation)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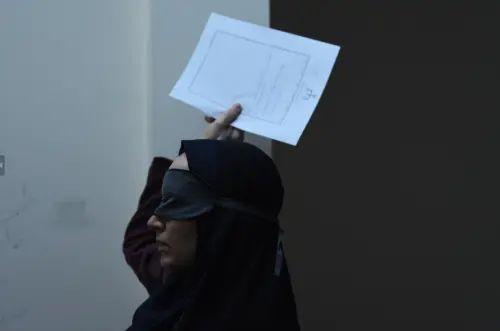
伊朗政治局勢的演變與藝術審查的惡化,來得又急又快。阿巴斯走了、醜聞被爆出;伊朗政府繼續緊盯潘納希疫,他還繼續拍;法哈蒂幾度登峰造極。
2020年,疫情前的最後一屆柏林影展,《無邪》最後一部競賽片放映,一舉奪得金熊獎。四段式電影,圍繞著監獄發生的四段故事,死刑行刑官、逃兵、執行死刑的士兵...,直接了當的對獨裁政治的審查做出了很好的批判。怎能不動容?當年有很多人很討厭這部片。政治批判電影和政治宣傳電影(propaganda)只有一線之隔。Rasoulof從來就不滿足於只拍一部電影。當伊朗政府卻一部片都不讓他拍。
伊朗在疫情後發生了因為「頭巾革命」有了因女權而起的大規模各種社會示威,擴及範圍之廣、程度之深、延續之久,這不只是女性主義運動,卻是能根本性地針對地方貪腐、特權階級、世代革命,法哈蒂時代的伊朗電影單向的倫理劇可以蘊含的複雜問題,如今全面向的爆發,我們也不用再通過單一窗口認識伊朗了。
Rasoulof 這次拍了快三個小時的故事,幾乎只發生在車上、一間市區住宅、鄉下小屋,毫無早期作品的生澀、習作、臨摹感,也沒有《無邪》、《不能說的再見》的因陋就簡,對我來說更多的是《正直好人》裡面那種典型的男性創作者在情節電影上面對「體制」的憤怒時,能否適度平衡電影感與正義感的拿捏。這次一點都不枯燥,甚至很像商業電影,很法哈蒂,有些典型坎城爆紅政治電影的氣味。但,這部片的賣座與口碑,太過商業、太過反正宣(變成另一種政宣),這些疑惑最終都會會與作者真正的赤誠錯身而過的,因為Rasoulof從來就不滿足於只拍一部電影。因為,Rasoulof從來就不滿足於只拍一部電影,他下一部電影將在德國漢堡開機。就像電影的片頭字卡提示我們的:菩提的種子會在寄主樹上發芽、抽枝、茁壯,逐漸將其窒息;然後,新的菩提樹就獨立存在了。或許,美學上,這就也是無論在哪塊土地都能發芽土壤的一種方式。
評審團獎、女主角獎:Adriana Paz, Karla Sofía Gascón, Selena Gomez, and Zoe Saldaña《Emilia Pérez》
《大獄言家》賈克歐迪亞(Jacques Audiard)有口皆碑的《Emilia Pérez》,實際上是四個女演員一起拿獎,但「跨性別」演員Karla Sofía Gascón上台領獎時卻誤以為是自己獨得影后,只因歌壇天后Selena Gomez和資深演員Zoe Saldaña都未到場領獎。
《Emilia Pérez》描繪來烘托一個黑幫大佬想要變性、贖罪的故事。片名已經暗示故事主角是誰,但本片確實沒有一個明確的主角,讓這部借用了墨西哥幫派暴力背景的西語歌舞通俗劇,儘管加上了主要人物Emilia變性前後的心路歷程,為讓在Emilia身旁的女人,被綁架的女律師(Zoe Saldaña)、Emilia Pérez還子的母親(Selena Gomez)、現在身旁的同性戀伴侶(Adriana Paz),來烘托變性與贖罪的故事。實際上,如果沒有歌舞場面,沒有大牌明星助陣,相比熟稔這類類型操作的阿莫多瓦,儘管Karla Sofía Gascón投注了自身迷人的「跨性別」經歷,歐迪亞這次在寫實主義故事的疏忽與傲慢,其實是顯而易見的。即便如此,筆者還是替如此「男性」的導演,在主流電影舞台,為性別多樣敘事盡一份心力感感到開心。

男主角獎:Jesse Plemons《Kinds of Kindness》
尤格蘭西默《Kinds of Kindness》其中一段故事讓整片「肝臟」癱在地上,才能說明這部片,就是他的「婚姻故事」。但這也沒什麼,柏格曼的《婚姻場景》也是六個小時。別忘了《婚姻場景》電視迷你劇是。用當代劇情片的規模與規格,《Kinds of Kindness》獲得迪士尼旗下探照燈影業的支持,把一個適合影集多段的故事拍出來,確實是一番成就,更別提本片精彩的卡司Emma Stone、Willem Dafoe、Margaret Qualley、Joe Alwyn,影帝Jesse Plemons才在《帝國內戰:美國內戰》剛交出令人印象深刻的配角演出,就用本片大篇幅(實際上甚至跟Emma Stone一樣多)且精湛的戲份,獲得一座實至名歸的坎城影帝。
故事中晦澀的晦澀、深慟,讓人不禁擔憂起導演Lanthimos的演員妻子Ariane Labed,陪伴演Lanthimos走過數部希臘「怪浪潮」電影,在Lanthimos於英語電影的主流世界高飛時,更多年耕於導演創作領域。Labed首部長片《September Says》同樣入圍坎城,卻在「一種注目」競賽。《Kinds of Kindness》三段曖昧不明的故事,那麼廣泛無邊,高深莫測,令人不禁聯想起導演的生命故事;本片編劇是Efthimis Filippou,Lanthimos許久沒有再攜手的編劇搭黨,或許合作關係,也是一種夫妻關係的投射。
現場影評似乎都執著在蘭希默回歸早期風格的失敗,也沒人想認真討論明明擺在桌上,他要深入的「主題」,就像那片肝臟。
最佳劇本:《The Substance》by Coralie Fargeat
結合女性主義敘事與女性剝削電影獲好評的《The Substance》,電影片尾大撒的血漿另所以影評人人稱道,卻比較少人認真討論本片真正的「Substance」應該是女演員的身體,本片用樸實的敘事、平滑的影像,像是真的在一個「換身」物質的廣告片般的精緻,用寬銀幕的震撼,拍出Demi Moore對衰老的恐懼,和Margaret Qualley肉體的青春。老實說,這些我們都在柯能堡電影裡面看過。卻不曾用女性主義敘事來拍過沒錯。事實上,儘管獲得最劇本,但若想看Demi Moore和Margaret Qualley的雙女主演出,對身體政治做出視覺的詮釋,恐怕觀眾會失望吧。還不如去看Qualley前年的cult爽片《聖地》(Sanctuary)。由男導演執導,《聖地》在台灣並沒有上映Qualley在片中扮來自底層的SM女王,與小開上演階級翻轉的戰爭,這點與Qualley真實生活中的「星二代」身份互文,則更顯趣味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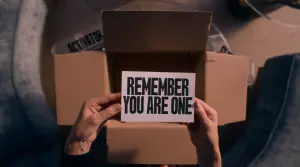
Miguel Gomes無疑的是許多影迷的英雄,這部片用一個逃婚官員、追逐他的未婚妻的故事,故事分為兩個部分,迷人的第一部分是大英帝國官員的部分,混雜了記錄、檔案資料、片場重演,美輪美奐。第二部分,則切換成追逐他的未婚妻的視角,重演更多了經典老片的氣味,故事層次更多,紀錄性的「旅遊文學」成分減少,詮釋人物心境功能則越來越少,越來越曖昧。
電影全片放映完,觀眾可能還需要時間咀嚼電影看似簡單,卻難以一言道盡的結局。這是一部讓世界大戰前、疫情前、疫情後的各種時間,用電影疊加、壓縮、釋放的現象學過程,殖民主義與後殖民主義是電影第一部分的切入觀點,但加入了不同性別、不同時間的向度之後,第二部分女性觀點的對照,究竟是解釋了、解脫了、解答了什麼嗎?Gomes無疑的拒絕給出明確的立場和直白的答案。讓這部,他首次攻頂坎城競賽的作品,成為他創作生涯中無疑「最困難」的一部長片。

Payal Kapadia的《All We Imagine as Light》是一個看似比想像中更質樸的作品。《All We Imagine as Light》故事描述,一對護士室友,帶著各自的感情煩惱,幫著「被都更」的醫院廚娘搬家,各懷心事的三人來到海灘的舒心與解放之旅。許多人問,「這究竟有什麼好拍的?」實際上,我問這部片和阿比查邦《極樂森林》有什麼差別?導演自言,在描繪女性的慾望、印度社會對女性慾望的壓抑之外,這還是一個關於「友情」的故事,既然是關於友誼,就是「女人不要為難女人」的故事。
若看過導演一鳴驚人的「實驗」紀錄片《A Night of Knowing Nothing》就知道他不會輕易放棄社會批判。《A Night of Knowing Nothing》用實驗電影手法,後設自傳性質描繪的一起校園和平抗議事件,針對當時電影學院校長的抗議,後來被警察鎮壓,用詩意手法描繪「運動後」的PTSD和感傷。這層感傷,或許在《All We Imagine as Light》無法明顯看到,只剩下一小段「都更聯盟」集會,但導演仍舊是那個關注在大的社會變動下,個體之間如何連結、維繫、保護情感,照料且不擠壓彼此慾望空間的作者。

當坎城的我們(通常是男人)一邊在罵尤格蘭西莫《Kind of Kindness》太過男性、太過重複,回想年初,我們是怎麼面對社群上《可憐的東西》是否是「女性主義」的爭議,在這些對「性」、「潛意識」的討論越來越開放,我們還剩下什麼不能揭露的戰場?如果一個跟隨潮流的觀眾、一個探看風向的KOL既不能喜歡《Kind of Kindness》、也不能喜歡《All We Imagine as Light》,那他今年該推崇哪部片?《Anora》?對我而言,蘭西莫一路走來始終如一,儘管靠向好萊塢商業迷失了一些風格,但他和他的編劇夥伴對佛洛伊德的理解始終沒有長進,卻與其他坎城男孩俱樂部導演一樣,越來越是當今美學的領航者,今天能對他有這些反省,當然難能可貴。
我們對蘭西莫的反省,是建立在對世界各種族群、種族、階級脈絡下的女性主義創作者夠深刻的理解嗎?
辨識、慎選你的戰鬥,或許這就是友誼可以給我們的最好意義,《All We Imagine as Light》最美妙之處在於,即便她的女性主義討論基本,但踏實。導演甚至提到,他是為了「All We Imagine as Light」這句話很美,而把它加入電影台詞,在電影末段一場阿比查邦感強烈的場面中,而這也是全片我們看到從寫實主義過度到魔幻寫實的驚鴻一瞥。
這給我們一個啟示:或許,「魔幻寫實」的發生並不一定在創作上是來自極端嚴格的田野調查、完全正確的身份政治審查、絕對道德至上的社會關懷;卻可以是一個內在平靜寬厚的作者,來自私人的、文學的、感性的片刻,讓自己被想像成光,在電影現場,照亮影像。若電影的想像力能讓我們找到一個,化解當代性、後現代性、寫實倫理與形式主義衝突的可能曙光,我們汲汲營營尋找那道光,其實可能就是每天在那裡的日出、夕陽。
●作者:沈怡昕/影評人
●本文為作者評論意見,不代表《NOWnews今日新聞》立場
●《今日廣場》歡迎來稿或參與討論,請附真實姓名及聯絡電話,文章歡迎寄至:opinion@nownews.com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