編而優則導的金鐘編劇徐譽庭去年聯手新銳導演許智彥,完成了叫好又叫座的《誰先愛上他的》,不但票房亮眼,更斬獲了金馬獎和台北電影節的多項大獎。拍了電影、拿了獎、一夕爆紅之後,三十而立的許智彥回顧從殺青酒、入圍、得獎、到慶功宴這一連串如夢似幻的旅程,不禁疑惑著:「自己長大了嗎?」
身為電影人的好處之一,是可以將所有的人生思考透過影像來作答,「最近正在重整一個關於『長大』的腳本,想拍出這個世代年輕人的樣子,恰好譽庭姊也叫我想想成長的故事,所以今年我會拼命接廣告和MV,趕快存錢回去拍電影。」一身街頭潮流感的許智彥,坐在工作室的長木桌前,笑著吐露渴望重回片場的真心話,那笑裡帶著開朗、陽光,有如少年。
兩年前,從未有執導電影經驗的許智彥,在對導演所需要的基本功,如劇本、導戲、鏡頭調度等一知半解的情況下,投入了《誰先愛上他的》的拍攝工作。電影開拍前,他看著邱澤與謝盈萱分立桌子兩側,排演那幕關鍵的叫囂、互罵的對手戲時,曾經非常困惑,完全無法判斷他們表演的好壞。
許智彥的難以適應,都被曾編導多部膾炙人口好戲的徐譽庭看在眼裡,她有時會扮黑臉,以言語揭露主角深處的瘡疤,帶出演員的真實情緒,催化出那種增一分太濃、少一分則太淡的完美化學反應。許智彥也因此知道,導演必須要敏銳地感知演員的心理狀態,才能掌握劇情節奏。「譽庭姊有幾次先提早離開片場,故意留下我跟邱澤相處,直到電影拍完後,我才後知後覺理解原因。」
 ▲《誰先愛上他的》製作過程如電影劇情般高潮起伏。(圖/許智彥提供)
▲《誰先愛上他的》製作過程如電影劇情般高潮起伏。(圖/許智彥提供)
《誰先愛上他的》籌備一年、拍攝32天、斥資超過千萬,但初期剪輯的成品,幾乎要把許智彥淹沒。因為機會難得,他太用力於影像美學,以至忽略了人物情感的傳達和鏡頭品質的細節。那段期間,許智彥每天一起床就立刻去公司,十幾個小時不斷檢視自己的失敗影像,嘗試剪出不同版本,但業界資深人士看了皆搖頭嘆息,最糟糕的時候,「譽庭姊已經打算把片子封存,然後去銀行貸款還債。」幸好徐譽庭改變了主意,她把自己從導演轉換回編劇的角色,將素材打散重組,最終剪輯版本大幅切換觀點,終於讓電影起死回生。
這部瀕臨腰斬到最後被救回的作品,2018年11月在台灣上映,一個月後票房即突破五千萬佳績,隨後便在台北電影獎一舉拿下包括最佳劇情長片、最佳男女主角等大獎。當年金馬獎也入圍八項重要獎項,最後由謝盈萱封后,李英宏《峇里島》獲得最佳電影原創歌曲,雷震卿拿下最佳剪輯。
 ▲李英宏為電影量身訂做的主題曲《峇里島》獲得金馬獎最佳電影原創歌曲的肯定。(圖/許智彥提供)
▲李英宏為電影量身訂做的主題曲《峇里島》獲得金馬獎最佳電影原創歌曲的肯定。(圖/許智彥提供)
製作過程如電影高潮起伏,而退潮後走回日常,許智彥意識到自身轉變。他綽號叫Kidding,像小孩一樣的白目又愛哭,曾在殺青酒把邱澤弄得不爽還不自知,或常在慶功宴時淚崩發表感言。但參加多次活動、影展、酒會後,許智彥開始討厭從前的自己,也不願再哭。然而,每當別人異常熾熱的眼光投射在自己身上時,又被迫穿上從前的許智彥外衣,「所以我在想什麼是長大?是去扮演他人認為你該有的樣子嗎?」
因為一無所有,只能放膽創意
許智彥認為要發揮創意,重點在於沒包袱。邱澤曾真心對許智彥說,羨慕他的一無所有、沒知名度,所以可以去犯錯。許智彥也羨慕自己,因為第一次拍電影不用扛預算、不用滿足外界期待;從前他跟李英宏在唯思影像工作時,兩人還是無名小卒,所以敢放手大玩MV創意,因為搞砸也沒人聞問。
「像當時跟顏社老闆迪拉提案蛋堡的《史詩》MV,我就在會議室裡比手畫腳,要拍一鏡到底,光想就覺得很好玩,雖然成品還是跟理想有差距。反之,現在有經驗、有預算,怎麼好像就少了一點生命力。」
 ▲蛋堡《史詩》MV挑戰一鏡到底的拍攝手法。(圖/許智彥提供)
▲蛋堡《史詩》MV挑戰一鏡到底的拍攝手法。(圖/許智彥提供)
他回憶畢業後,憑著憨膽投稿MC HotDog《不吃早餐才是一件很嘻哈的事》MV。當時極度渴望創作被看見,沒錢、沒演員,還是憑著狂熱一頭栽入,只用一台Canon相機就下海自導自演。因為無法請來歌手,他帶著動物頭套在早餐店演出,奇異手法配合著歌詞節奏,有種無俚頭的融合感,立刻被慧眼相中。
MV獲選後,顏社老闆迪拉找他加入新成立的WIZ唯思影像製作班底,專門拍攝嘻哈MV,立刻圓了街舞少年的MV導演夢想。有時他也會想,若當初沒投稿,現在會在哪裡?
 ▲MC HotDog《不吃早餐才是一件很嘻哈的事》MV無俚頭卻極具風格。(圖/許智彥提供)
▲MC HotDog《不吃早餐才是一件很嘻哈的事》MV無俚頭卻極具風格。(圖/許智彥提供)
去年台北電影獎慶功宴結束,徐譽庭曾對許智彥說,拍片還是窮窮地拍好,「就像你的MV,真是越窮拍越好。」許智彥也反思,為什麼現在缺少用創意奮力一搏的生命力?以前五萬、十萬的案子拼命接。現在一個五十萬的案子,團隊反而會羅列出一大堆問題。「我老婆說我們是不是有大頭症?她說若今天譽庭姊再來找拍片,是否會嫌錢少?」
近期徐譽庭出資,讓許智彥團隊嘗試去拍一個本《嘻哈爸爸》,「譽庭姊希望能把團隊帶回以前《台北直直撞》那種匱乏但解放的狀態,當時根本沒在管場地申請,走到哪就拍到哪。」徐譽庭挑明只給低預算,不覺得沒錢是限制。許智彥說,這感覺其實很嘻哈,歌手像永遠長不大,一無所有,但很有魅力。
 ▲拍攝《台北直直撞》MV時,即使資源匱乏卻能創作出奔放的作品。(圖/許智彥提供)
▲拍攝《台北直直撞》MV時,即使資源匱乏卻能創作出奔放的作品。(圖/許智彥提供)
讓自己活在創作的影像裡
「愈靠過往經驗,找愈多參考案例,拍攝愈精準,反而成果不好。」許智彥說前幾天拍廣告很不順,因為每個環節、走位、表情都被精心設計,但反而很假。今年高雄電影節VR拍攝邀約,讓許智彥短暫逃離創作低潮。他回到父親成長的台南新營老宅拍攝,從已過世祖母的視角,一鏡到底紀錄家族成員之間的真實互動。許智彥笑說,當天導戲判斷異常精準,他在現場還會調侃大伯不要假裝演戲。「當天拍攝過程很舒服,節奏很慢。場景裡每個人都是真實的,都是在演自己。」
拍攝中場休息時,許智彥足歲的兒子在庭院嬉鬧,鳥在樹林間鳴叫,眾人和緩地在鏡頭外休憩,彷彿也活在框景內。「對我而言,電影最迷人的不是鏡頭內,而是在鏡框之外。」許智彥形容這是一種不可思議的感受,但只要現場能捕捉到這樣的氛圍,即便未看到成品,就知道會成功。
「我蠻渴望能在每部片子裡有話直說,也渴望裡面都有真實。」像拍攝手遊廣告《那些年,終將逝去的青春》,三個男孩間的青春悸動、嬉鬧喧騰,同樣埋藏許智彥的真實生命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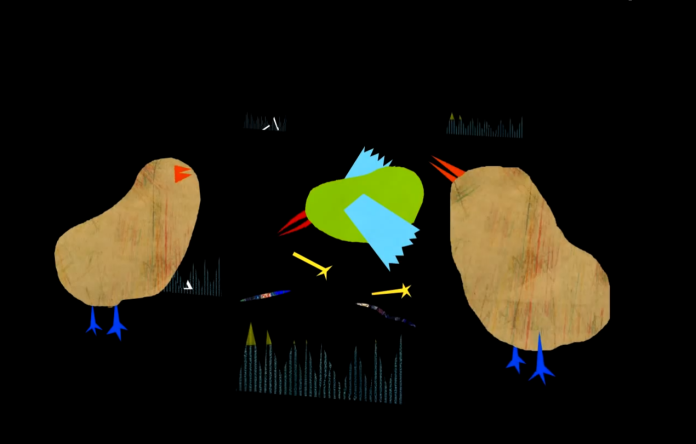 ▲拼貼動畫作品《Nature》潛藏著許多自己的深刻情緒。(圖/許智彥提供)
▲拼貼動畫作品《Nature》潛藏著許多自己的深刻情緒。(圖/許智彥提供)
2008年許智彥前往紐西蘭留學,隔年做了名為《Nature》的拼貼動畫,故事描述一隻小鳥受傷被兩隻大鳥照顧,變茁壯後想飛走,但大鳥們不願意,又把小鳥腳咬斷。不到兩分鐘影像,潛藏濃烈的真實情緒,內容隱喻前女友的離去,也回應離家對父母感受。
迷惘徬徨,讓人有話要說
出身小康家庭,父母、姊姊都是高材生,家族中長輩更不乏國外頂尖學校畢業,任職政府高層。許智彥不諱言求學時有壓力,但不像上一代人辛苦,雖未能享受名牌,但至少不愁吃穿。
「萬芳姊就曾問我,是不是沒有吃過苦?可能是我們這一代人天生流露出的感覺。」許智彥觀察他這個世代,困擾的不是柴米油鹽,而是人生目的,煩惱要篩選哪些資訊到頭腦,衡量自己在社經階層的百分比。
回自己的母校實踐大學教書超過五年,許智彥撞見千禧世代謹慎、苦悶與疑惑,已經很努力,但未來為何是這樣?「拍《台北直直撞》時,我就想呈現年輕人有話要說,但說了、PO了也沒人聽的狀態。所以MV裡,我讓李英宏在馬路上大喊『台北』,但又沒有人鳥的畫面。」
許智彥坦言自己的創作仍處於徬徨而未解的狀態,他帶著想解脫低潮束縛的語氣說:「我真的是人生第一回,好像有機會能說自己要說的事。彷彿重回多年前的大學畢製,但這次沒老師罵你、指導你,也沒時間限制。」
 ▲學生時期入圍金穗獎的動畫《以我之見》。(圖/許智彥提供)
▲學生時期入圍金穗獎的動畫《以我之見》。(圖/許智彥提供)
雖然想拍電影的心異常濃烈,但許智彥也矛盾沒勇氣拍下一部,不確定自己是否能扎實地說完兩個小時的長篇故事?回顧學生時期入圍金穗獎的動畫《以我之見》,當時義無反顧的質疑萬物,即便內容晦澀不明,但保有「有話想說」的衝動,生澀中傳達真實的張力。
在經歷人生首次導演電影後,關於「何謂長大?」的疑問,或許沒有解答,但他依然真誠的直面自我,即便不再是從前的Kidding,卻彷彿始終未變。
我是廣告 請繼續往下閱讀
兩年前,從未有執導電影經驗的許智彥,在對導演所需要的基本功,如劇本、導戲、鏡頭調度等一知半解的情況下,投入了《誰先愛上他的》的拍攝工作。電影開拍前,他看著邱澤與謝盈萱分立桌子兩側,排演那幕關鍵的叫囂、互罵的對手戲時,曾經非常困惑,完全無法判斷他們表演的好壞。
許智彥的難以適應,都被曾編導多部膾炙人口好戲的徐譽庭看在眼裡,她有時會扮黑臉,以言語揭露主角深處的瘡疤,帶出演員的真實情緒,催化出那種增一分太濃、少一分則太淡的完美化學反應。許智彥也因此知道,導演必須要敏銳地感知演員的心理狀態,才能掌握劇情節奏。「譽庭姊有幾次先提早離開片場,故意留下我跟邱澤相處,直到電影拍完後,我才後知後覺理解原因。」
 ▲《誰先愛上他的》製作過程如電影劇情般高潮起伏。(圖/許智彥提供)
▲《誰先愛上他的》製作過程如電影劇情般高潮起伏。(圖/許智彥提供)《誰先愛上他的》籌備一年、拍攝32天、斥資超過千萬,但初期剪輯的成品,幾乎要把許智彥淹沒。因為機會難得,他太用力於影像美學,以至忽略了人物情感的傳達和鏡頭品質的細節。那段期間,許智彥每天一起床就立刻去公司,十幾個小時不斷檢視自己的失敗影像,嘗試剪出不同版本,但業界資深人士看了皆搖頭嘆息,最糟糕的時候,「譽庭姊已經打算把片子封存,然後去銀行貸款還債。」幸好徐譽庭改變了主意,她把自己從導演轉換回編劇的角色,將素材打散重組,最終剪輯版本大幅切換觀點,終於讓電影起死回生。
這部瀕臨腰斬到最後被救回的作品,2018年11月在台灣上映,一個月後票房即突破五千萬佳績,隨後便在台北電影獎一舉拿下包括最佳劇情長片、最佳男女主角等大獎。當年金馬獎也入圍八項重要獎項,最後由謝盈萱封后,李英宏《峇里島》獲得最佳電影原創歌曲,雷震卿拿下最佳剪輯。
 ▲李英宏為電影量身訂做的主題曲《峇里島》獲得金馬獎最佳電影原創歌曲的肯定。(圖/許智彥提供)
▲李英宏為電影量身訂做的主題曲《峇里島》獲得金馬獎最佳電影原創歌曲的肯定。(圖/許智彥提供)製作過程如電影高潮起伏,而退潮後走回日常,許智彥意識到自身轉變。他綽號叫Kidding,像小孩一樣的白目又愛哭,曾在殺青酒把邱澤弄得不爽還不自知,或常在慶功宴時淚崩發表感言。但參加多次活動、影展、酒會後,許智彥開始討厭從前的自己,也不願再哭。然而,每當別人異常熾熱的眼光投射在自己身上時,又被迫穿上從前的許智彥外衣,「所以我在想什麼是長大?是去扮演他人認為你該有的樣子嗎?」
因為一無所有,只能放膽創意
許智彥認為要發揮創意,重點在於沒包袱。邱澤曾真心對許智彥說,羨慕他的一無所有、沒知名度,所以可以去犯錯。許智彥也羨慕自己,因為第一次拍電影不用扛預算、不用滿足外界期待;從前他跟李英宏在唯思影像工作時,兩人還是無名小卒,所以敢放手大玩MV創意,因為搞砸也沒人聞問。
「像當時跟顏社老闆迪拉提案蛋堡的《史詩》MV,我就在會議室裡比手畫腳,要拍一鏡到底,光想就覺得很好玩,雖然成品還是跟理想有差距。反之,現在有經驗、有預算,怎麼好像就少了一點生命力。」
 ▲蛋堡《史詩》MV挑戰一鏡到底的拍攝手法。(圖/許智彥提供)
▲蛋堡《史詩》MV挑戰一鏡到底的拍攝手法。(圖/許智彥提供)他回憶畢業後,憑著憨膽投稿MC HotDog《不吃早餐才是一件很嘻哈的事》MV。當時極度渴望創作被看見,沒錢、沒演員,還是憑著狂熱一頭栽入,只用一台Canon相機就下海自導自演。因為無法請來歌手,他帶著動物頭套在早餐店演出,奇異手法配合著歌詞節奏,有種無俚頭的融合感,立刻被慧眼相中。
MV獲選後,顏社老闆迪拉找他加入新成立的WIZ唯思影像製作班底,專門拍攝嘻哈MV,立刻圓了街舞少年的MV導演夢想。有時他也會想,若當初沒投稿,現在會在哪裡?
 ▲MC HotDog《不吃早餐才是一件很嘻哈的事》MV無俚頭卻極具風格。(圖/許智彥提供)
▲MC HotDog《不吃早餐才是一件很嘻哈的事》MV無俚頭卻極具風格。(圖/許智彥提供)去年台北電影獎慶功宴結束,徐譽庭曾對許智彥說,拍片還是窮窮地拍好,「就像你的MV,真是越窮拍越好。」許智彥也反思,為什麼現在缺少用創意奮力一搏的生命力?以前五萬、十萬的案子拼命接。現在一個五十萬的案子,團隊反而會羅列出一大堆問題。「我老婆說我們是不是有大頭症?她說若今天譽庭姊再來找拍片,是否會嫌錢少?」
近期徐譽庭出資,讓許智彥團隊嘗試去拍一個本《嘻哈爸爸》,「譽庭姊希望能把團隊帶回以前《台北直直撞》那種匱乏但解放的狀態,當時根本沒在管場地申請,走到哪就拍到哪。」徐譽庭挑明只給低預算,不覺得沒錢是限制。許智彥說,這感覺其實很嘻哈,歌手像永遠長不大,一無所有,但很有魅力。
 ▲拍攝《台北直直撞》MV時,即使資源匱乏卻能創作出奔放的作品。(圖/許智彥提供)
▲拍攝《台北直直撞》MV時,即使資源匱乏卻能創作出奔放的作品。(圖/許智彥提供)讓自己活在創作的影像裡
「愈靠過往經驗,找愈多參考案例,拍攝愈精準,反而成果不好。」許智彥說前幾天拍廣告很不順,因為每個環節、走位、表情都被精心設計,但反而很假。今年高雄電影節VR拍攝邀約,讓許智彥短暫逃離創作低潮。他回到父親成長的台南新營老宅拍攝,從已過世祖母的視角,一鏡到底紀錄家族成員之間的真實互動。許智彥笑說,當天導戲判斷異常精準,他在現場還會調侃大伯不要假裝演戲。「當天拍攝過程很舒服,節奏很慢。場景裡每個人都是真實的,都是在演自己。」
拍攝中場休息時,許智彥足歲的兒子在庭院嬉鬧,鳥在樹林間鳴叫,眾人和緩地在鏡頭外休憩,彷彿也活在框景內。「對我而言,電影最迷人的不是鏡頭內,而是在鏡框之外。」許智彥形容這是一種不可思議的感受,但只要現場能捕捉到這樣的氛圍,即便未看到成品,就知道會成功。
「我蠻渴望能在每部片子裡有話直說,也渴望裡面都有真實。」像拍攝手遊廣告《那些年,終將逝去的青春》,三個男孩間的青春悸動、嬉鬧喧騰,同樣埋藏許智彥的真實生命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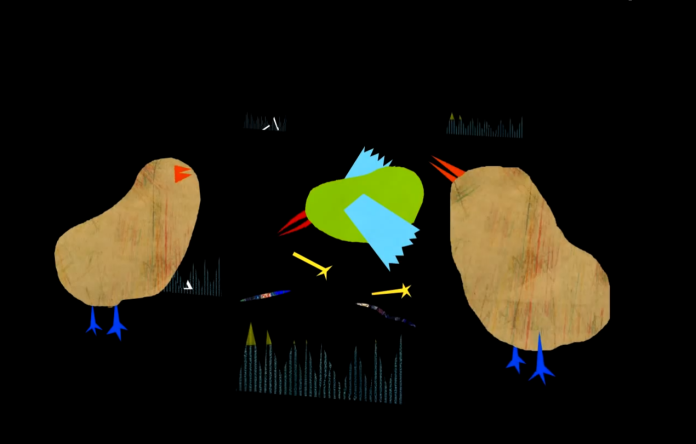 ▲拼貼動畫作品《Nature》潛藏著許多自己的深刻情緒。(圖/許智彥提供)
▲拼貼動畫作品《Nature》潛藏著許多自己的深刻情緒。(圖/許智彥提供)2008年許智彥前往紐西蘭留學,隔年做了名為《Nature》的拼貼動畫,故事描述一隻小鳥受傷被兩隻大鳥照顧,變茁壯後想飛走,但大鳥們不願意,又把小鳥腳咬斷。不到兩分鐘影像,潛藏濃烈的真實情緒,內容隱喻前女友的離去,也回應離家對父母感受。
迷惘徬徨,讓人有話要說
出身小康家庭,父母、姊姊都是高材生,家族中長輩更不乏國外頂尖學校畢業,任職政府高層。許智彥不諱言求學時有壓力,但不像上一代人辛苦,雖未能享受名牌,但至少不愁吃穿。
「萬芳姊就曾問我,是不是沒有吃過苦?可能是我們這一代人天生流露出的感覺。」許智彥觀察他這個世代,困擾的不是柴米油鹽,而是人生目的,煩惱要篩選哪些資訊到頭腦,衡量自己在社經階層的百分比。
回自己的母校實踐大學教書超過五年,許智彥撞見千禧世代謹慎、苦悶與疑惑,已經很努力,但未來為何是這樣?「拍《台北直直撞》時,我就想呈現年輕人有話要說,但說了、PO了也沒人聽的狀態。所以MV裡,我讓李英宏在馬路上大喊『台北』,但又沒有人鳥的畫面。」
許智彥坦言自己的創作仍處於徬徨而未解的狀態,他帶著想解脫低潮束縛的語氣說:「我真的是人生第一回,好像有機會能說自己要說的事。彷彿重回多年前的大學畢製,但這次沒老師罵你、指導你,也沒時間限制。」
 ▲學生時期入圍金穗獎的動畫《以我之見》。(圖/許智彥提供)
▲學生時期入圍金穗獎的動畫《以我之見》。(圖/許智彥提供)雖然想拍電影的心異常濃烈,但許智彥也矛盾沒勇氣拍下一部,不確定自己是否能扎實地說完兩個小時的長篇故事?回顧學生時期入圍金穗獎的動畫《以我之見》,當時義無反顧的質疑萬物,即便內容晦澀不明,但保有「有話想說」的衝動,生澀中傳達真實的張力。
在經歷人生首次導演電影後,關於「何謂長大?」的疑問,或許沒有解答,但他依然真誠的直面自我,即便不再是從前的Kidding,卻彷彿始終未變。



